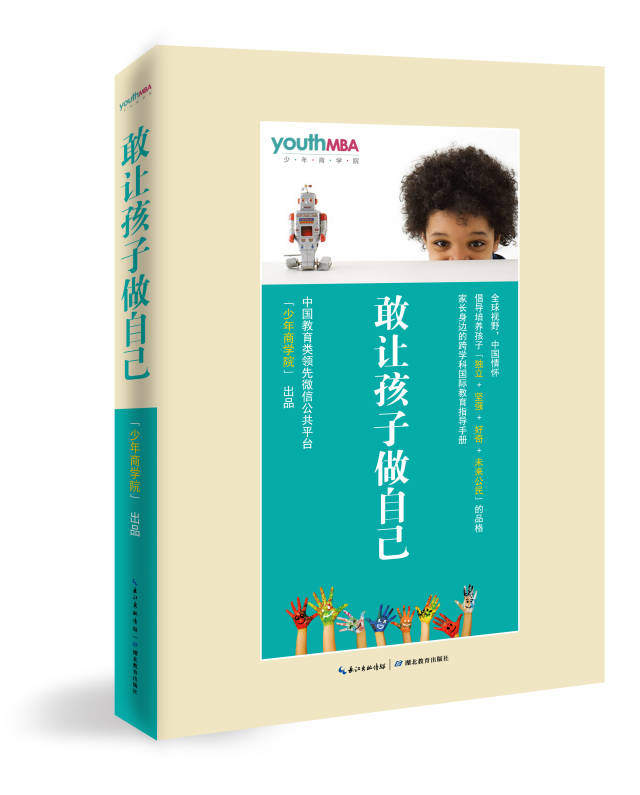“对我影响巨大的书籍,和我安身立命的专业无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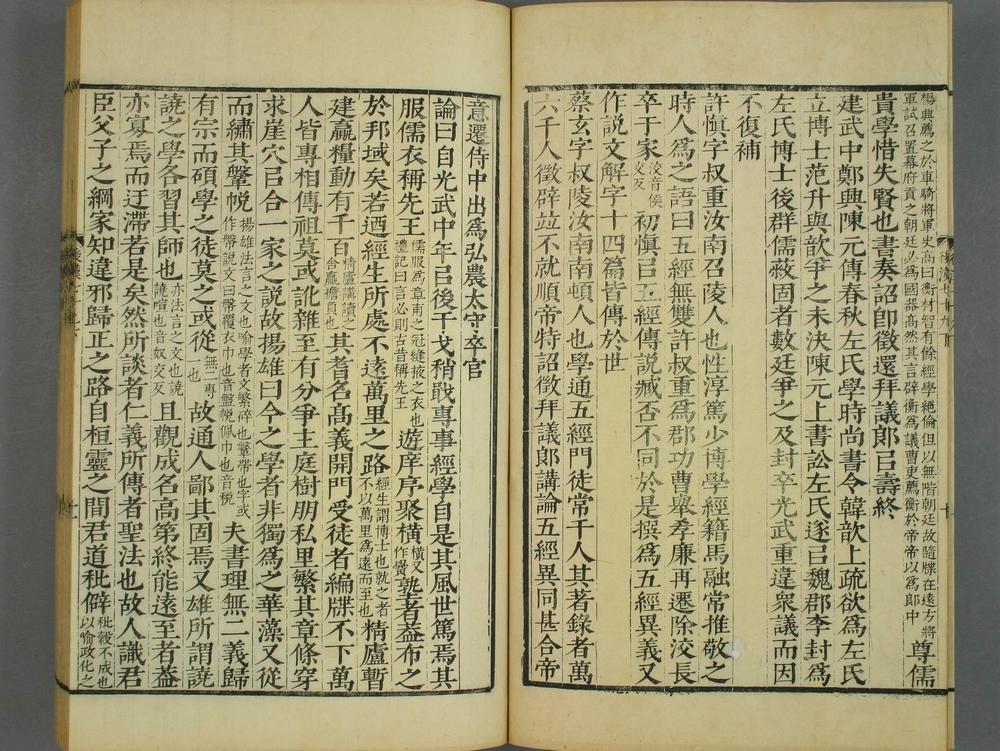
这是少年商学院微信(ID:youthMBA)第33篇分享文章,作者钟伟为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原文刊发于南方周末。我们已与之联系授权。
最早的时候,被迫读的是《三字经》之类的东西,父亲早逝,母亲读过一点私塾,但识字和文化都不多。《三字经》的重要性在于,它让作为孩子的我,知道了我的祖先是谁,我应该有怎样的善恶之分和克己反省的习惯,我应该如何对待父母亲戚朋友。这比现在幼儿园就灌输小孩爱国爱党,成人后才被劝诫不要随地吐痰,要好得多。
我在30岁之后才接触到《大学》,恍然觉得《三字经》或者千字文原来和这些经典,是一脉相通的。其意不正,其心不诚,对待自然和社会所产生的偏差,不是大学文凭能抵消的。基于这样的原因,我对中国中小学教育非常担心,师生的压力都很沉重,学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头奶牛,老师和父母的期望只是通过教育挤出哗哗的分数之奶,学生被大量程式化的反复练习,毫无意义地被折磨得奄奄一息。这种社会病态很可怕。
在我的中学阶段,阅读得比较多的是古诗词,其中《诗经》尤其令我喜欢。上世纪70年代的县城里有一所小小的图书馆,其中《林海雪原》和《李自成》等最受欢迎,但却非常乏味,另外就是一些前苏联和法国作家的作品,我比较喜欢大小仲马,大仲马是个讲故事的高手,基于这一点,高中时读到金庸,觉得两人堪可一比。
图书馆的书不多,我的小人书不少,我就在戏馆前开了个小人书摊,1-2分钱看1本,淡的时候一天赚两三毛钱,好的时接近两块钱。书摊的收入,部分用来增加新的小人书,另外就是买我喜欢的其他书籍,例如诗经、楚辞,左传,诗三百,唐诗别裁,宋词别裁,香山居士集,淮海居士集,万首唐人绝句等等一大堆。我曾买过一本臧克家做序的《绝句一百首》,老先生在序言说,自君之出矣,不复理残机,思君如满月,夜夜减清晖,这样的怨妇思夫,小孩怎么懂呢?没关系,死记硬背就行,因为长大后回想起来自然就懂了,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懂得愈多样愈复杂。而长大后你很有可能不再有充裕的时间去背诵。因此在中学期间我就死读死背了不少书籍,让我终生受益良多。在这些书中,我最喜欢的是《诗经》以及曹操的古诗。诗经中感情的纯粹优美,如同雪山清泉。
有露珠的青草,我喜欢的女孩,宛如清扬般走来。
苍茫的芦苇,渐寒的白露,我爱的人啊,你在哪里?
花儿开了,娇艳呵,你在哪里?花儿开着开着快凋谢了呵,你在哪里?
我爱的人呵,长眠在树下,冬天了,他在地下会冷吗?
无论用何种姿态翻阅《诗经》,那种震撼人心之绝美,常常让我无言,甚至恍惚觉得,《诗经》一出,便已是不可逾越的绝响。
基于这样的经验,我也让我的孩子钟天行从小开始阅读,他最喜欢的是《三国演义》和《资治通鉴》(白话本),也爱读隋唐水浒之类。读东周列国时,天行说,从国君到义士,这些人杀来杀去,几乎看不到好人。接近春秋无义战的本意了,在很多时候,也许是成人低估和扼杀了孩子成长的天空。
中学到大学期间,我更喜欢阅读一些哲学书籍。其中《道德经》《通向奴役的道路》和《政府论》对我而言极其重要。因为平素是自己乱读书,全凭兴致所之。譬如我不太喜欢《论语》,原因在于我总觉得董仲舒和朱熹两人,装神弄鬼地不像正常人,其诠释也未必正道。凡读《红楼梦》,我必跳过书中大堆诗词,因为那些香艳低俗不忍卒读。
据说《道德经》是仅次于《圣经》的、全球发行量第二大的读物。人们通常总是走老庄之路,把它当作文字作品来看待,而没有走黄老之路,把《道德经》作为伟大的政治哲学来看待,或者说,在我看来,《论语》对个人修身养性大有裨益,但对治国几乎无用,而《道德经》似乎是世外智贤对君主的训示。历代儒生对《道德经》的篡改和伪读实在多了点。
例如,老子从没说过“无为而治”,而是说“为无为”,也就是按照事情本来的规律那样,去治理国家。这也就更容易理解为什么老子说治国如“烹小鲜”,而不是生吞活鱼。无所作为和胡乱作为的政府,都是不可取的。儒生和皇帝总相互吹嘘“不教而化,不行而治”,是为皇帝偷懒不好好工作找借口。例如老子说,“使民重死而远徙”,后世儒生篡改为“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老子本来的侵略性的、扩张性的治国理念,就被改成了躲在君主父母身边的犬儒计策了。我常常以为,《道德经》包含了对人性和政府的深深怀疑,对自然的敬畏,以及一种因彻底绝望而产生的有克制的乐观主义。
在我的大学期间,西方哲学思潮席卷而来,其中五角丛书可能深深影响了一代人,萨特的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尼采的意志论和罗尔斯的正义论,都是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所钟爱的。我武断地认为,那个年代的青年不会拒斥学术讲座,但会拒绝于丹式电视书场;不会热烈拥抱海子舒婷,但会瞧不上琼瑶迷们,不会停止对哲学的好奇,但却始终无法摆脱对政府、对权力高度警惕而厌恶的烙印。
这时,两本书给了我迷惘思考的某些清晰答案。即《通向奴役的道路》和《政府论》,当时我看到的《通向奴役的道路》是红色封面的节译本,其中对专制和集权的鞭挞,对自发扩展秩序的解释,给我以光明的想象。哈耶克、米塞斯、林赛等的论著,在十多年后,才由中国社科院的一批青年学者组织系统翻译出版,是我一直珍视和保存的。《政府论》对什么是政府、政府为什么必须有限并且要置于监督之下、政府的组成和职能给予了清晰的论述,约翰·洛克连同大卫·休谟等一道,很大程度上澄清了我阅读卢梭和伏尔泰时的困惑,尤其是卢梭对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对政府的无限幻想,常常让我怀疑卢梭,怀疑他所主张的政府要么是纯洁的神府,要么将堕落向邪恶。
此后我逐渐走上了职业经济学家的道路,专业书籍的阅读比例越来越大,对文学哲学的阅读有所减少。经济学、金融学的大量书籍是形而下的,我从来未能接受“金融是经济的核心”这样的观点。通过阅读,我知道书籍很多,但值得一生阅读的也许不多;我知道沉迷于电视报纸的头版头条,更容易让人成为神志不清的“知道分子”,而不是拥有自觉灵魂的知识分子。如果说有什么书不得不提,那么《热力学统计》和《资本论》也都十分重要,前者诠释了自然界,后者诠释了人性和经济活动的关系。
年过四十之后,我有了系统读经的愿望,但心力修为浅薄,让我读得多,偶有所得,读懂的却甚少。其中《心经》《大涅槃经》是必读的入门,我并非想去皈依,而是试图触摸彼岸,寻找灵魂的家园。
林林总总这些,对我影响巨大的书籍,似乎和我养身立命的专业无关,但我却以为深刻地塑造了我从事专业研究的基点。作为人,我们知道什么呢?我们的无知是无限的。
所以,放下现代性的傲慢,去回望我们的家园。在我的孩子10岁时,我对他说,每天看五分钟新闻联播、非诚勿扰之类,坚持十年,这个人仍将是一无所知的废物,每天五分钟,读一点经典,学几句法语,同样十年,这个人将有一技之长。人生是一种习惯,甚至只是一种阅读习惯,因为天堂大致就是图书馆的模样。
阅读是一种力量,让我们安静地存在。尼采说,上帝死了,然后,福柯说,人死了。所以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必须好好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