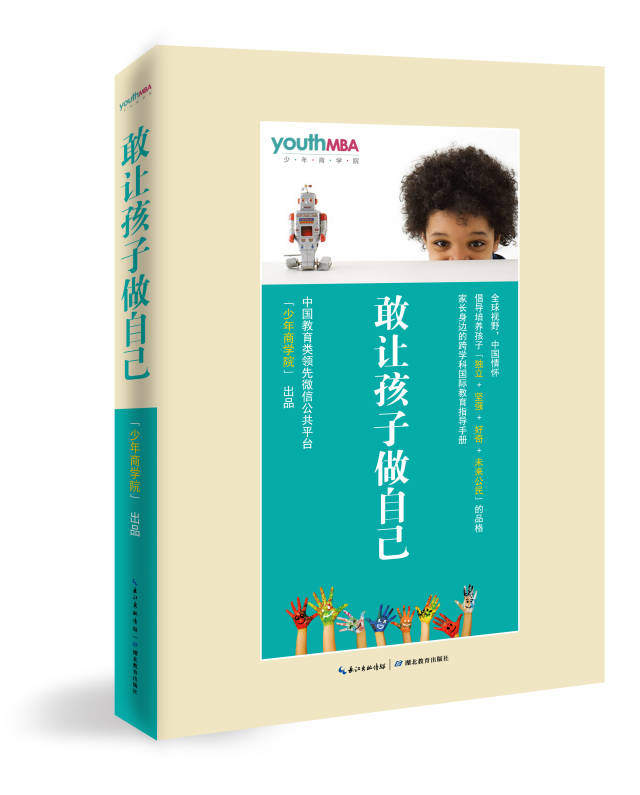玩音乐,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
 这是少年商学院微信(ID:youthMBA)分享的第153篇文章,转载自纽约时报中文网,作者陈复加是牛津大学动物学博士、科学松鼠会会员、现为某F1车队材料工程师。小提琴十级,牛津大学Hertford学院、Exeter学院交响乐团小提琴手。我们已经与她联络授权。
这是少年商学院微信(ID:youthMBA)分享的第153篇文章,转载自纽约时报中文网,作者陈复加是牛津大学动物学博士、科学松鼠会会员、现为某F1车队材料工程师。小提琴十级,牛津大学Hertford学院、Exeter学院交响乐团小提琴手。我们已经与她联络授权。
我17岁那年在上海虹桥一个琴行打工,工作是在周末担任小提琴教师,学生多为附近街区的小孩,从3岁到15岁不等。每一个学生都有一个类似的故事:不识音律却望子成龙的家长,希望孩子学习音乐以开发智力,每周风雨无阻送孩子来学习,回家仔细督促。孩子们虽然时有抵触,却也在家长们的殷切下进步明显。我谨记着小时候的小提琴教师的说法:“学琴是童子功”,也如此振振有词地对着我的学生家长说:“7岁开始已经晚了,10岁就算了……”
直到有一天,琴行来了个25岁的空姐。我皱着眉头重复着说辞,空姐却一脸恳切:“我从小就希望学习小提琴,但一直没有机会。现在有点积蓄也有点时间了……”琴行经理本着“顾客就是上帝”的原则,一定要我收下这位空姐为学生。我勉强开始上课,却发现空姐的作息因着工作极为不规律,经常因为工作而缺课,练习时间也不长。虽然她聪明悟性好,积极性也非常高,但进度并不快,让身为教师的我情绪颇为消极。空姐大概意识到我的态度,渐渐地不来上课了。由此我也更加坚信,音乐学习属于智力发展迅速、又有空余时间和家长督促的孩子,背负着社会家庭责任、没有多少余暇的成人是难以成功学习音乐的。
到英国后我发现我错了。在牛津读博士的一天,同学威廉邀请我晚上去参加他父亲的威尔士男声合唱音乐会。我满心以为他父亲是个专业音乐家,为可以省一张昂贵的音乐会票而沾沾自喜。夜里进入教堂,才发现这个“牛津威尔士男声合唱团”纯属业余组合。这个合唱团始于牛津汽车工业蓬勃发展的20年代,许多威尔士工人背井离乡来此工作,因思念家乡而组建起一个威尔士语的合唱团。如今本地汽车工厂大部分已经关门搬去中国和印度,但合唱团却成功地传承下来,团员多为本地普通老人,只因热爱歌唱而走到一起。这些普通农民、杂货店店主、清洁工、建筑工人,穿上红色西装,打上白领结走上舞台,有的还颤巍巍拄着拐杖。当他们共同唱起一曲《The Lord’s Prayers》,我也忍不住为他们喝起彩来。
威廉却眨着眼说:“精彩的还在后头。”演唱会结束后,团员们来到教堂边的酒吧,纷纷解开领结脱去外套,恢复为酒吧里常见的本地工人红脸豪爽的模样。不同的是,他们端着酒杯,三两组合,开始自发唱歌。有些曲目在演唱会时已经听过,有些是更为通俗的民间小调。威廉的爸爸端着一个一升装的酒杯,头发蓬乱,大手掌不停拍着身边的同伴,洪亮的声音浑厚有力,眉眼中却都堆着笑。酒吧中的其他顾客们纷纷为他们鼓掌,我也深深为其感染,这是一群多么热爱音乐的老人们。
当我离开校园,开始朝九晚六周末加班的生活后,我也曾对着蒙尘的小提琴哀叹,心想自己再无机会继续学习音乐了。但同事史蒂芬妮却不这么认为。作为一个生物化学工程师,史蒂芬妮有一份全职的忙碌工作,还有一对不满一岁的双胞胎儿子。家庭和工作的繁琐未曾磨灭她的音乐梦。她从零开始学习小提琴,每周坚持去老师家上课,每天下班后在家练习。她也曾抱怨过琴声吵醒了儿子们,她只能放下琴去照料啼哭一夜的孩子。丈夫及时给她送上礼物——一把可调音量的电子小提琴,顺利解决了矛盾。儿子们一岁生日时,史蒂芬妮亲自为儿子们演奏一曲《祝你生日快乐》。我很难去挑剔她尚需雕琢的琴技——音乐是她寻求内心平静的工具,是回归自我的伊甸园的途径,又何必让精益求精的训练损害她的快乐?
我的上司布莱恩想要的则更多。年逾六旬的布莱恩是公司的首席工程师,也是个狂热的古典音乐爱好者。他的汽车收音机永远停留在BBC的古典音乐频道,也会不厌其烦地与乘客普及各类音乐八卦,使得公司同事出差都害怕与他同车。他热爱演奏小号,无论工作多辛劳,每周都抽出一个晚上在镇上的交响乐团排练。他还满心希望去参加邻近另一个镇上的交响乐团,“那个乐团的指挥更好一些,”但他紧接着又不无惋惜地说,“我太太只允许我每周有一个晚上不在家……”
布莱恩的目标是退休后能像凯什一样生活。凯什早年从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成为华威大学工程系的教授与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创办并参与经营过两个高科技公司。退休后的他卸下所有科学重任,拾起他对单簧管的爱好,进入英国公开大学攻读音乐硕士学位,以其扎实的学术基础研究起单簧管历史,甚至还就此发表过一些论文。如今他进入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攻读音乐博士,并在四个交响乐团里担任单簧管演奏一职。退休于凯什而言,是可以有时间进入另一个领域继续钻研。年纪与时光在他们面前如同浮云,于他们的音乐爱好毫无影响。
在英国,热爱古典音乐的老人们就像喜爱地方戏剧的中国老人一样普遍。我的博士答辩老师法兰克是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材料系荣誉教授及系主任,在全球材料学领域也是赫赫有名的学者。他最大的爱好是演奏萨克斯,曾经在英国的萨克斯演奏竞赛中获奖。每年在给系里学生的欢迎与毕业宴会上,他都会亲自为大家演奏萨克斯。有一次法兰克主持一个在伦敦举办的学术会议,主办方正讨论邀请什么乐队在会议的宴会上演奏,他自告奋勇:“我带我和我的爵士乐队伙伴来演奏,不要你们的演出费。”他满心以为可以为主办方省了经费,却没想到将所有乐器从谢菲尔德搬到伦敦的费用,已经超过伦敦当地乐队的演出费。这让主办方头疼了好久,直到秘书壮起胆子,请法兰克打消了演奏的主意。为此法兰克嘟囔了半个月。
有了这些前辈做榜样,年近30的我顿时失去了年龄的借口。我开始批驳自己曾经的“唯年龄论”,承担着社会责任的成人们失去了家长的外力逼迫,却有爱好作为自己的学习动力,这难道不是最佳的学习方式吗?我开始梦想去修一个兼职音乐学位,也很想找回当年的空姐学生,为当年的偏见与她道个歉,希望她后来找到了一个比我宽容得多的老师,可以一圆曾经的音乐梦。
就在这篇文章成稿的这一天,我收到老同学威廉的邮件,邀请我去参加他父亲的“最后一场音乐会”。70岁的父亲被诊为晚期胰腺癌,将不久于人世。合唱团的朋友们准备在医院里为他举行最后一场音乐会,让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能放声歌唱,用音乐与友情来慰籍脆弱易逝的生命。这真是我所见过的最美好的告别礼物。